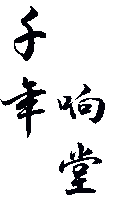响堂山永远的隐痛
2023-11-02 08:18:34

白晓东
邯郸西南,进入太行山之前,一座山横亘于斯。这就是鼓山,又名响堂山,著名的响堂山石窟建造在此。
响堂山石窟,开创于北魏,建于北齐(公元550-577年)。彼时,北齐定都于邺,以晋阳为别都。位于鼓山脚下的太行八陉之一——滏口陉,成为北齐王朝权贵往来于两都的必经之处,这里商贾云集,驿使星流。
北齐把佛教奉为国教。由于鼓山石质优良、山水秀丽,皇帝高洋不惜人力物力,选择在这里开窟建寺,营建行宫,遂造就了法相庄严、美轮美奂的响堂山石窟寺。此后,历经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,响堂山石窟的雕凿敲击声断断续续,千年不绝……响堂山石窟不仅是北齐石窟艺术的集大成者,更是我国石窟艺术史的缩影,有“中国第五大石窟群”“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一”和“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”的赞誉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《中国通史》中发出一声感叹:“响堂山石窟可以与龙门宾阳洞、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冈各大窟相媲美!”。1959年,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视察峰峰矿区,路上听闻将途经响堂山石窟时,临时决定,冒雨前往,参观完后连说:“这是国宝!应该很好地保护它,艺术价值很高!”
1961年,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,响堂山石窟赫然在列。
一
然而这“千年响堂、神山福地”,却有着自己永远的隐痛。
对敦煌莫高窟,有一个千古罪人——道士王圆箓。敦煌的经卷、唐塑、写本等,几乎都因他而流失海外。对于响堂山,同样也有一个千古罪人,不同于王圆箓的无知、短视、愚蠢,他堪称精明、远见,或者说是狡猾,此人便是卢芹斋。
1880年,卢芹斋生于浙江湖州卢家渡,这里是真正的江南腹地,评弹软语,杂花生树,粉墙黛瓦。看其相片,确是江南男子的样貌,文质儒雅,尤其眼神,如莫测深潭。
卢芹斋出身微*,父亲嗜赌,以致家道衰落,母亲含恨自尽,不久,父亲去世,他成了孤儿。机缘巧合,卢芹斋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——浙江南浔张家二少爷张静江,成为张家的仆人。张静江非等闲之辈,祖上是安徽休宁人,家族经商,到张静江祖父张颂贤时,张家真正成为富商大贾。南浔镇上有“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”之说,赚100万两银子只是条小黄狗,象的标准是1000万两。张颂贤去世时,已经是“四象”之一。一脉传承,到张静江这一辈,干脆把生意做到了国外——张静江是第一个在法国开商行的华人。他在巴黎开办的“通运公司”从中国运销茶叶、绸缎、地毯、漆器,以及古董、字画,“获利之巨,无法估计”。1905年8月,张静江乘坐海轮去往法国,在甲板上他遇到了一个可以改变彼此命运的人——孙中山。两人一见如故,通过交谈,张静江对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自古官商不分家,商是官的助力,官是商的保障,张静江看明白了这一点。于是,张静江对孙中山说:“我会倾尽全力支持革命事业!”孙中山没有想到,此非戏言,而是黄金白银的实捐真赠。之后,发生在广州黄花岗的武装起义、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清廷官员良弼、关东起义等行动,无一不是得到张静江的大力资助。后期,因为所费甚巨,张静江的商业活动深受影响,他默默卖掉了巴黎的茶叶店,以及上海的几处洋房。
张静江的付出终是得到了不错的回报:他成为革命家,官至财政部部长、国民政府代理主席,孙中山称他为“革命圣人”,后世则称他为“国民党四大元老”之一,可谓是名利兼收。聪明如卢芹斋看明白了这一点,在心里默默谋划着自己的未来。在后厨做饭的他,干活利索,尤其懂得张静江的眼色和脸色,摸准了他的口味和脾气。
1902年,幸运之神再次垂青这个有着狂野之心的青年——卢芹斋作为唯一侍从,跟随时任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的张静江来到巴黎,在其开设的“通运公司”做学徒,刻苦学习古董行的各项业务、规矩,同时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、法语。卢芹斋逐渐被提拔为掌铺,他的各项能力有了一个质的提升,为日后建立自己的古董帝国埋下扎实的伏笔。
1908年,卢芹斋历经九年历练,对于政商两界和明暗规则已是驾轻就熟。此时,张静江回国协助孙中山继续革命,“通运公司”宣告关张。
二
时机终于成熟,羽翼丰满的卢芹斋决定大干一番,开办了自己的古董店——“来远公司”,之后又注册成立“卢吴古玩公司”。此时,只有二十八岁的卢芹斋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孤苦无依、看人脸色、强颜欢笑的张家仆人,世界在他面前正缓缓展开,属于他的主场时刻终于到来了。1909年,卢芹斋在巴黎的生意刚刚起步,表现得不温不火,他的内心有些焦急,因为这和他扬名立万、买办中西的目标尚有不小的差距。恰在此时,巴黎赛努奇博物馆馆长向卢芹斋展示了几张响堂山石刻佛像照片,并表示出极大的兴趣。这几张照片,不啻于漆夜里的一道闪电,霎时照亮了他的“前途”。
卢芹斋敏感地察觉到佛像所隐藏的巨大商机,他当即决定一探佛像究竟。隔天,卢芹斋给北京公司分号寄去这些照片,并且暗授机宜……几个月后,北京公司分号找到八尊出自响堂山的真身大小石刻佛像。这些佛像辗转运至巴黎后,自然买给巴黎赛努奇博物馆,卢芹斋从中大赚了一笔。尝到甜头的卢芹斋由此开始真正的佛像盗卖生意。也就是说,早在1910年左右,卢芹斋就已经开始觊觎响堂山,从时间上推定,正是在响堂山,他挖到了最重要的第一桶金。
1922年,日本人常盘大定考察响堂山之时拍了很多照片,从照片看,响堂山石窟寺内部佛像大多残缺不全。也就是说,这短短十几年间已有大量佛像被盗卖,其中不仅有整件的佛像,还包括单件的佛头。尽管这十年间,还有查尔斯·维涅、埃德加·沃尔希、山中定次郎、迪克兰·克莱肯等古董商涉足响堂山石窟佛像的买卖,但种种迹象显示,卢芹斋盗卖响堂山文物不仅时间最早,而且盗卖量最大,他对于响堂山石窟文物的破坏可谓空前绝后,使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蒙受巨大损失。除了响堂山的文物,卢芹斋倒卖的国内文物珍品还有很多,甚至包括被鲁迅先生称为“前无古人”的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——昭陵六骏中的“飒露紫”和“拳毛騧”。卢芹斋的“来远公司”成为中国古董在欧洲的最大集散地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卢芹斋在美国纽约又开一间中国古董店。自1915年起,向美国出口文物长达三十多年,贩卖国宝不计其数。可以说,中国几乎一大半的文物是经卢芹斋手远涉重洋,流落异邦。
1913年和1914年,民国政府颁布禁止和限制文物出口法令,但卢芹斋的生意一点未受影响,他对自己的买卖从来直言不讳,背后的靠山不用猜,大家也知道是张静江。如果卢芹斋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古董贩子,那么事情也就变得简单,对于他的行径只需口诛笔伐,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后人永远唾弃即可,但世间的人事又哪里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?
1937年7月,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作为中国人,卢芹斋也投入了爱国行动,动员在巴黎、纽约的公司全体职员捐出大量现金。他的夫人玛丽·罗斯担任战争遗孤救济会的财务工作,为中国难民和伤员提供救济。看到很多初到法国的留学生生活艰难,卢芹斋叮嘱其公司经营的“万花楼饭店”,每天向中国留学生免费提供一顿午饭。1937年10月,卢芹斋前往日内瓦,参加当地中华妇女联合会举办的义卖,提供9件拍卖品,义卖获得收益全部贡献给中国红十字会,用于救助战争受难者。1938年1月,卢芹斋在伦敦赞助了一场中国文物展,收入全部捐献给美国医疗援华会。
1943年,宋美龄受美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之邀,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,卢芹斋是受邀听众之一。1947年,在学者陈梦家的鼓动下,卢芹斋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河南洛阳出土的战国青铜器“嗣子壶”。在此之前,陈梦家赴美留学撰著《流散美国的中国铜器集录》,卢芹斋为其多方周旋打通关节,取得调查的第一手资料。此外,他还邀请知名学者伯希和对中国文物进行研究并出书(古玉图录、青铜器图录等),这些研究成果让外国人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文化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卢芹斋又是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启蒙者。
三
虽然卢芹斋在国家存亡这样大是大非面前,似乎有着清醒的头脑,作出了貌似正确的选择,但,瑕不掩瑜的同时,瑜也一定不能掩瑕。
卢芹斋认为:“艺术没有国界”“环游世界的艺术品就像是不说话的外交使节,它们让其他民族了解中国,热爱中国。”卢芹斋在晚年曾试图为自己辩护,出口的文物都是市场上通过与别人竞标买来的,且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。如果它们留在中国,还不知会遭到怎样的毁灭厄运。按佛家说法,成住坏空是必然,然而必然中,又有偶然。没有卢芹斋,会不会有其他的李芹斋、王芹斋……这些文物倘若留在国内,能顺利躲过一场场战争、运动和浩劫吗?被盗卖异国是错,那毁在国内算不算错?卢芹斋的话,像是一种自我安慰、刻意掩饰,终究难掩他内心的种种虚弱。那么,到底该如何评价卢芹斋?
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说:“综清末民初鉴藏家,其时其境,与项子京、高士奇、安仪周、梁清标不同。彼则楚弓楚得,此则更有外邦之剽夺。亦有因而流出者,亦有得以保存者,则此时之书画鉴世故家,功罪各半矣。”
无疑,张伯驹是大度旷达的,是简而化之的,但往事并不如烟,功过并不相抵(何况有些“功”还需打上大大的问号),有些过错是无论如何也弥补修饰不了的。
1948年7月29日,卢芹斋的最后一批货物被截留于上海——共17箱、342件文物,其中不少属于国宝级珍品。这场意料之外的变故,对于年近七十的卢芹斋来说可谓致命一击。
1950年3月,卢芹斋在纽约发布声明:“我已年过七十,经营中国古董达半个世纪……我收购的大批文物在上海被查封,其中包括我至关重要的藏品,这令我意识到,我的古董生意已经山穷水尽,无以为继……因此,我不无遗憾地决定,从此退出古董交易这个行业。”卢芹斋的纽约古董分店由他的同僚弗兰克·加罗接收,法国巴黎古董店由他的小女儿接管。1957年,78岁的卢芹斋在瑞士去世。至此,卢芹斋的“事业”落下帷幕,一代文物走私巨头所留印记似乎烟消云散。
但,真的会烟消云散吗?
四
大佛洞前的西边群山如龙虎腾跃,山岚隐约,四周清寂。响堂山仿佛一个沉默的老人,遥想着当年的光风霁月,也历数着自己的伤痕累累。
此刻,几万里外,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、在费城宾大博物馆、华盛顿弗利尔-赛克勒美术馆……不知又有多少慕名而来的人,在柔光轻抚的响堂山艺术珍品前流连赞叹。
他们可曾感知到响堂山的痛?记得那个叫卢芹斋的人?
上一条:“我想回家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