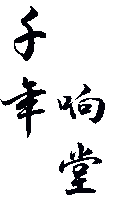响堂寺:山静林郁,车马不尘
2024-06-20 18:29: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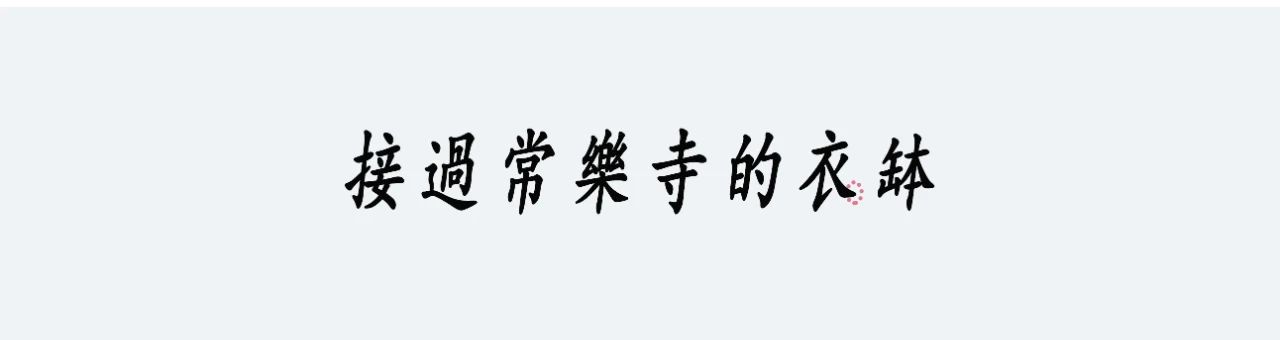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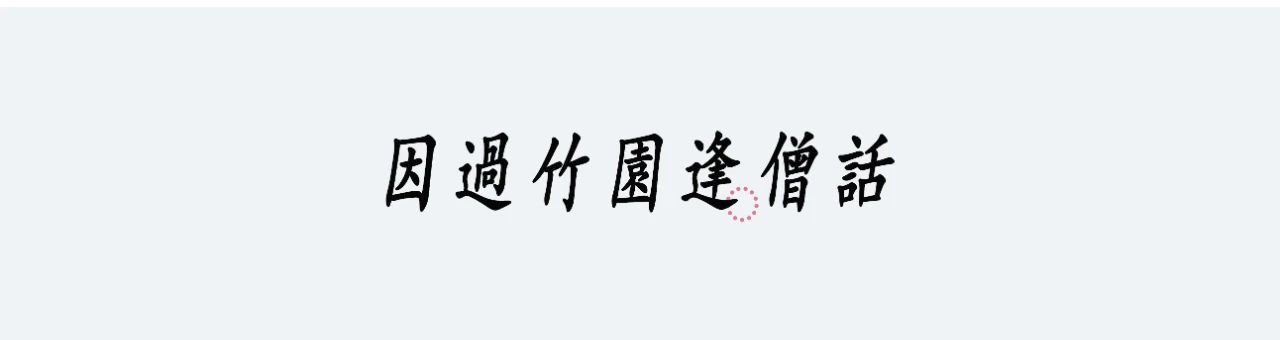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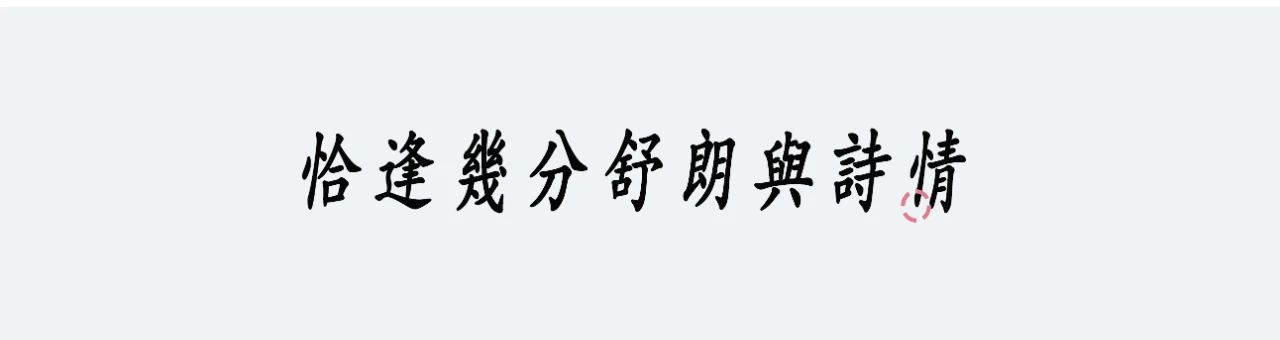

寺有什么特别?让寺不仅是寺的,自然是它的精神源流。寺院大殿屋顶的瓦当和滴水远看一片青灰,近看却也有着种种玄机——这瓦当上的莲花,滴水上的忍冬纹,都是来自山腰间石窟里那些一千四百多年前镌刻的纹路。这些瓦当、滴水于细微处完成了某种物质和气韵的双重衔接,使响堂寺在精神上完成了对响堂山的庄重皈依。
寺院室内和廊道内的地砖色如墨玉,踏上去不滑不涩,赏心悦目。一问才知,这砖竟是与故宫太和殿所用一样,俗称金砖。金砖并非真的用金子制作,称为金,一是烧成后,质地坚硬,敲击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,故名“金砖”;二是与普通方砖相比,烧造工艺复杂,造价极为昂贵,因而民间唤其为“金砖”。这些金砖来自苏州的御窑金砖厂。一块金砖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方能最终烧制完成,铺砌的进度自然就慢,需要真正耐得了烦,静得下心,时间的磨砺在这里不禁令人感慨而又敬重。
石灯的原型来自比较接近北齐时期的寺庙实物,还有一种石灯,则源于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后驻锡的奈良唐招提寺。徜徉在这齐风唐韵中,会自然而然地猜想,在弥漫的夜色中,这一座座石灯在亮起的刹那,是否会让人有一种穿越感,只一瞬,便抵至北齐、大唐?

大雄宝殿上的三孔天窗,则是受大佛洞石窟西侧岩壁上的天窗孔洞启发。夕阳西下之时,阳光穿过天窗,正好洒在佛像的脸上,佛祖额头的宝石折射出斑斓的天光,使这大殿愈加显得庄肃、静穆。
响堂寺里的佛像全部由黄铜铸造,凝重的铜色把佛的崇高慈祥,菩萨的和善端庄,罗汉的温顺诚恳,天王的孔武有力,刻画得活灵活现。当伫立于一尊佛像前,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人渐渐平静下来,仿佛时空在这里慢慢凝聚,仿佛一切都在此刻静止,于是,佛静静地洞察着我们的祈愿,默默地聆听着我们的心事。

相较于石窟道上的游人如织,常乐寺遗迹处的众生的流连,响堂寺则有着另一种情致,那就是清幽静谧。
从经幢广场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华严殿、药师殿、兜率宫……
各个大殿,一一走过、看过,静笃地信众们跪拜蒲团之上,双手合十,默默念念。大概是想把心中的纠结苦楚,统统向佛菩萨倾诉。我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祈祷是虔诚的,他们的祝福是真挚的,不然他们不会躲开开阔与热闹,而来到这一个个安静的院落。
有人因为看到而相信,也有人因为相信而看到。寺里的虔诚信徒无疑属于后者。他们相信会得到帮助,这份“信”变成一股可以仰仗依赖的力量。

也有在寺里只是散步、静坐的人。不为问佛,只是在寺院中缓行,在树下、竹下休憩,借由此处幽静,洗刷周身浮躁。或许不带任何目的,只是在这寺里,便是最好的时光。脚踏实地把自己融在这一片清幽中,沐清风,闻梵音,看云影天光,看石上青苔,看根深叶茂,也看落花作尘。
响堂寺庙确乎有种难以形容的气场,让人敬,却不让人畏,让人欣,却又不至于喜。在这恰到好处的静定里,人心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自省,会不知不觉地遍生法喜。这弥漫天地的静,其实不止是耳边的无声,更是心中的无争。

在最后一个院落,我遇见寺里的师父。
清茶两杯,清香一炷,午后的阳光已有几分夏日的热烈,透过帘幕斜照在禅堂的地上,光束中有无数金色的纤尘在游移、在浮泛、在周转,每一粒微尘都是一个世界,不,应是三千大千世界……在这安静中,我开始了与师父的问答。
——是否有心重铸“河朔第一古刹”的辉煌?
——“河朔第一古刹”是名相,是世人的馈赠,却不可以去主动追求。世事无常,一切相皆是虚妄。有这样恋慕追求的心,还怎么静定一颗悟空的心?放下,一切皆可、皆需放下。无欲则无求,无求则无苦,无苦则无我,无我则包容万物。
——沧桑的“千年石窟”与崭新的响堂寺是一种什么关系?

——石窟代表过去,响堂寺代表现在,两者是一脉相传、衔接延续的关系。新与旧是相对的,也都是暂时的。成、住、坏、空,最终归宿皆是涅槃寂静。那些古寺、古窟,也有新成的一刻,不过漫漫时间终将那一层“新”渐渐销蚀、磨灭。跳出表象,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,那就是千年传承的精神。
——响堂寺的妙处是禅境清幽,响堂石窟的妙处是盛大煊赫,如何看待这一隐一显?
——人群蜂拥的石窟和常乐寺,其实背后都有两个不变的支撑,也就是宗教的精神和信仰的力量。我们拥有着眼前所显现的,一定要感恩背后所隐藏的。直白点讲,隐在石窟背后的响堂寺,才是显处响堂山的未来。
杯中的茶凉了,心头却有一丝温热。骤雨将至前的天色暗了下来,心里却又是一片明朗……

“向晚钟声来,唤醒梦中客。”
响堂寺的钟声响起,暮色开始群山之巅弥合。
不知不觉已近黄昏。